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对另一些人的不利影响。比如说,假如10%的人拥有所有的智能机器人,而这些人创造90%的GDP。但如果大多数人都失业了,也就没有购买力了。因为劳动力不再是让货币流入需求侧的主要因素,所以传统的经济模型都会失效。很多传统的经济指标可能失去功能。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比如很可能数据显示失业率上升了,经济决策者据此认为经济出现了衰退风险,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则是电脑和机器人取代了人的职位,故而经济会持续增长,并不会衰退。所以我们必须调整已有的模型来反映新的经济态势。
到2080年左右,很多经济部门将永久性地由AI运营。根据我的公司Supertrends的研究,到3031年,人类将可以把很多复杂工作全部交给AI去自动完成。比如理论上,到那时我们可以运送一批机器人去火星,在足够的算力支持之下,给它们安排任务,让它们把火星建设得和新加坡一样,到100年之后我们回去看时,会发现火星已经是一派现代城市的模样。
FT中文网:人类行为总会有伦理的一面,而AI可能不会考虑伦理问题,不会像人类一样遵守道德原则,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特维德:在AI产生自我意识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伦理保障机制,制定相关准则。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失误总会发生,比如某个恶意软件被发布。但我不认为AI会开始蓄意与人类作对。真正的危险是恶人带来的,比如恶人有了利用AI来牟利或作恶的机会。这跟互联网的情况完全一样,比如那些利用互联网来传播电子病毒的人,但这些人只占互联网使用者的极少数。基本问题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AI时代制止坏人的任务会变得更加复杂,不过底层的思路是不变的,如制定法律和规则,营造社会共识等等。
FT中文网:你提到了中国在发展AI方面的优势,但中国可能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不成熟、监管机制不完善、总体经济自由度不高等,而美国的经济体系可能更为完善——尽管目前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国如何解决潜在瓶颈,更好地利用本国优势?你对此有何建议?
特维德:人们常说美国在全球最擅长“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擅长“从1到N”的创新。我认为中国可以在“从0到1”的领域做出更多努力,为中小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创造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环境,创造一个大量年轻人勇于创业的商业环境。中国一向重视由政府确定战略产业和领域,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其中的一些领域,中国确实已经成长为全球领军者。但私人部门中的创新者能够发现政府所不知道的有发展潜力的领域,风险投资机构可以合作为这样的机会投资,并通过其专业融资能力从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创新企业的初始资金不足问题,并能加快创新进程。这两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好的结果。
当然不仅对中国来说如此,这也是全球性的普遍规律。激励创新有很多具体途径。比如,公司可以规定,任何员工都可以就如何利用AI优化流程提出建议。假如说这个提议能够每年为公司节省200万美元。公司接下来可以允许这位员工拿走这笔节省下来的钱,创设一个新的产品或服务。又比如风险投资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前18个月的运营资金,在企业成熟之后获得50%的股权。类似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的硅谷等地是行之有效的,也鼓励了超级创新的出现。这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FT中文网:你提到AI的发展可能给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带来巨大变化,可能促进这些市场的繁荣,那么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来更好地利用这些变化为自身服务?
特维德:中国可以采取措施,为中小创新企业上市创造更多便利,比如简化和缩短上市流程、放松过于严格的上市要求等等。美欧企业界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依然开放度不足。市场准入很重要,因为从事私募和风险投资的企业通常都希望能在几年内收回成本,然后转战其他大洲或国家。如果他们的这一愿望难以得到满足,他们也就从一开始不愿意大规模投资。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优化美国的市场准入流程。拜登执政时期对大企业跨国并购初创企业制定了过于严格的规定,这种垄断性的做法阻断了一些投资者收回成本的途径,于是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下一代的新科技。所以必须全景式地看到资金流入和流出一个国家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群体是企业家。比如特朗普政府中主管AI事务的官员、即“AI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就是美国的一位重要企业家,有在初创企业任职的经历,熟悉这个行业的内部结构,也知道如何发掘行业内的机会。这个任命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总之我们需要始终思考的是,在创业生态系统中资金是如何周转和流动的,以及如何增进这种流动性。
FT中文网:除了受国内因素影响之外,中国股市近年来也受到中美贸易战的间接影响,你对中国股市的未来是否持乐观态度?
特维德:是的。我对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前景都持乐观态度。目前中国股市中的盈利收益率显著高于长期国债利率,大多数股票的股息收益率也高于长期国债利率。从我长期的投资经历来看,如果股息收益率高于长期国债利率,就代表一个投资于股票的好机会。如果盈利收益率是长期国债利率的三倍以上,即股权溢价很高,也代表投资的好机会。同时中国银行存款总量是中国股市市值的三倍多。上次这种情况发生时,股市上涨了200%。如果我们设想未来中国股市上涨200%,在那种情况下,股票的盈利收益率依然要高于长期国债利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股市的确令人非常看好。
同时中国政府非常强调经济增长,与日本、韩国等国的政策相似,我们在欧洲称此为“亚洲增长模式”。当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也积累了很多债务,如果产能过剩问题持续下去,债务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面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人们不禁要问:中美间紧张态势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的职业经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说他不喜欢中国人。移民欧美的中国人犯罪率低,与当地社会深度融入,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所以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喜爱。所以中美之间为什么会紧张?我的观点是这归根结底是源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差异。
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0%,而美国这一比例为接近70%。美国经济是“消费者经济”,社会是由民众的消费需求驱动的。中国经济则是“投资者经济”,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也有出口导向倾向,对其他国家大量出口,这是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根源。要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你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因为他的言辞始终在频繁变化,比如今天痛斥某个人,后天又盛赞这个人。你必须听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官员和财政部官员的表述,才能明白他们在中美谈判中到底想要什么。比如罗伯特•莱特希泽说中国是全球最不平衡的经济体之一。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我觉得他实际的意思是说,中美两国经济都是不平衡的。美国需要一场“供给侧革命”,当初里根就想做这样的事,而目前美国需要做得更多,比如要鼓励对AI、造船业等行业的投资。中国则需要更多的消费。这才是美国真正试图实现的目标。我不清楚他们能否成功,但如果中美之间宣布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中国股市将会大涨。此前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后,这些国家的股市都出现了上涨,特别是越南。
FT中文网:美国对中美贸易流动施加了很多限制,美国还树立了科技转让壁垒,试图阻止中国获得一些先进科技。你觉得这对中国AI发展的实际影响将会有多大?
特维德:我觉得具体影响可以归结到一个因素上,那就是芯片。芯片问题无关贸易和关税,而是美国制定政策,规定一些对华芯片出口为非法。这对中国当然是一个不利因素,但它并不具有彻底扼杀中国产业发展的效果。在我看来,AI领域最具经济前景的是部分是“AI智能体”(Agentic AI),发展这种AI并不以拥有芯片为前提。如果你看看AI方面的全球算力,据估计目前美国大约占75%,中国大约占15%。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70年,这两个数字将变为45%和30%。但为什么要根据某项科技的投入量来衡量其重要性呢?应当根据科技创造的利润来衡量其重要性。算力是很昂贵的,这是一种投入,产出的利润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AI智能体广泛投入应用,那么在不需要多少算力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获得很多的利润。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AI人才,他们懂得如何在已有企业环境中操作和利用AI智能体,同时创造新的企业类型,这个国家将获得AI领域最大的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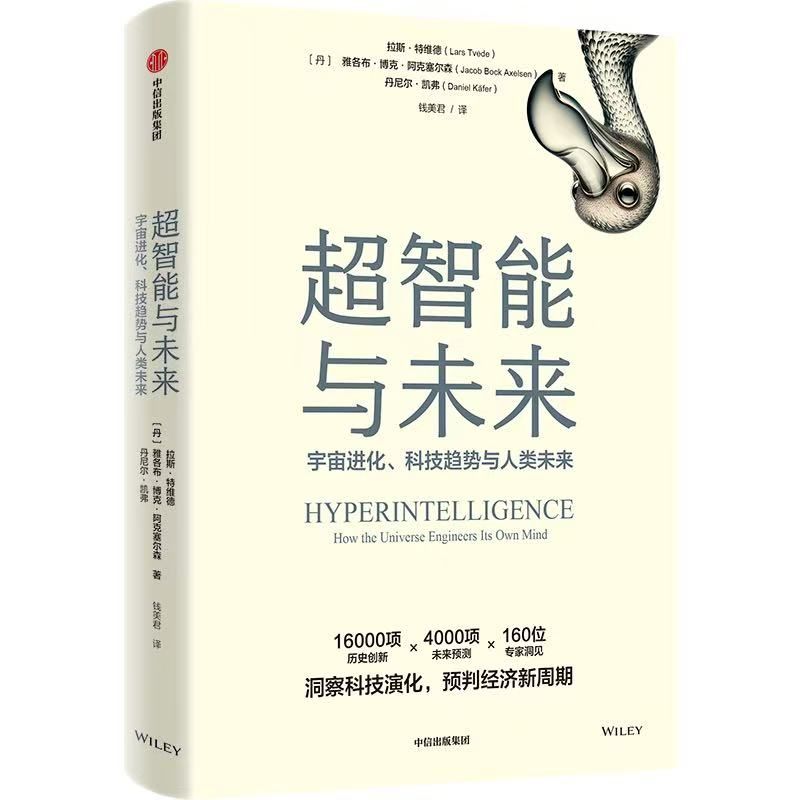
《超智能与未来:宇宙进化、科技趋势与人类未来》,[丹]拉斯•特维德、雅各布•博克•阿克塞尔森、丹尼尔•凯弗著,钱美君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出版。